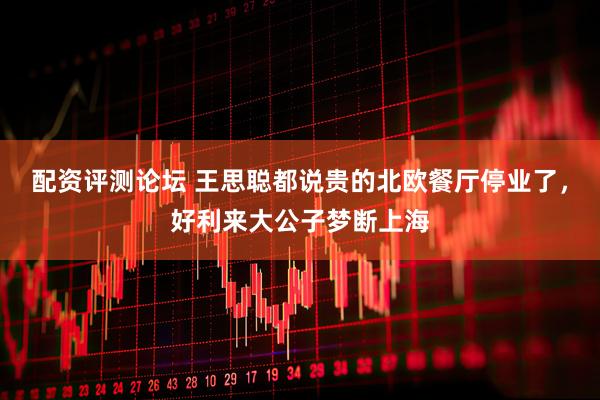2013年12月的一个清晨理财配资平台,北京西单附近气温逼近零度,室内却因为一幅《长征·七律》热闹起来。李讷拿着放大镜,几次凑近字里行间,忽然抬头,用带着湘音的普通话断定:“真的,真的,像父亲写的一模一样!”说完,她伸出手握住作者李坤泽,足足半分钟没松开。

这不是第一次有人把毛主席的笔迹“骗”过她的眼睛。可那一刻,李讷的神情与二十年前在河南郏县看到父亲手迹时几乎相同——先是惊喜,随后是追忆。李坤泽不好意思地解释:“是临的。”李讷笑道:“能临到我分不出真伪,也是本事。”
把时间拨回1966年。李坤泽出生在河南商水县,那是个连灯光都透着墨香的书香家庭。五岁起,他跟着父亲摹《九成宫》,写欧楷。部队生涯让他第一次系统接触毛主席诗词,气势磅礴的行草击中了年轻人的心。1991年,他决定潜心研究毛体,自此十年如一日,一页一页临,一笔一笔琢磨,“墨磨穿铁砚”并非夸张形容。

毛主席的字缘何让后人如此着迷?得从老人家少年入私塾说起。1898年前后,他在湘乡私塾抄《古文观止》,临《礼器碑》,师承钟繇,却又早早抛开束缚。到革命年代,战地行军桌子是膝盖,毛笔蘸烟灰也要写,笔画奔放,行气贯通。
1955年,北京天安门广场即将竖起人民英雄纪念碑。设计组在领袖递来的几幅信笺中反复比较八个字的排列。有工人嘀咕:“这么拆开重新排,会不会破坏行气?”雕塑家刘开渠给出办法:先放大,再用手工修飞白,保留笔锋原味,难题迎刃而解。“人民英雄永垂不朽”自此悬于广场中央,风吹雨打依旧劲挺。
四年后,1959年秋,毛主席从黄炎培处借来王羲之真迹。工作人员回忆,老人家工作间歇就端坐灯下,对照真迹描摹,常常把饭菜晾凉。黄炎培电话追问是否该归还,主席只回一句:“期限到,今天务必送回。”书法痴迷,可分寸分毫不乱。
另一件人人熟知的作品是“为人民服务”。1944年秋,张思德追悼会上,主席写下五个大字,随后被镌刻在新华门影壁,也印成无数像章。它不只是一句话,更像精神坐标。有人统计过,新中国前二十年里,这五个字出现频率位列所有标语第一。
正因为影响深远,“毛体”作为独立书法门类很快成形。1963年,山东学者贺惠邦最先提出“毛体”概念;1996年,潍坊有了全国第一家毛体研究会;到2008年,北京奥运会前夕,一卷两千零八米的毛体长卷刷爆国内外媒体。高峰时,全国大小毛体社团超过二百家,作品展几乎月月不断。
李静的故事常被青年书家提起。1950年,这位曾在朝鲜战场负伤的女兵回国领奖,毛主席握着她的手说:“你也姓李,是我的女儿。”从那以后,李静写字只学毛体,几十年后在历史博物馆举办个人展览,标题就叫《毛泽东思想光照千秋》。她用笔墨寄托对“父亲”的敬意。
国外同样有人迷恋这种线条。泰国前国会主席颇钦·蓬拉军收藏不少毛体条幅,他最喜欢毛主席引用的“不是西风压倒东风,就是东风压倒西风”。与李坤泽见面时,他略带兴奋地说:“东方必胜。”李坤泽顺手写下“东方压倒西方”,对方连呼“perfect”,可见魅力不分国界。

临摹达到真假难分,也引发新的讨论:怎样划定“真迹”与“再创作”的界线?国家档案馆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数字扫描原件,分辨率逐年提高,一旦有人拿复制品冒充真迹,专家只需比对“飞白”微痕便能见分晓。保护原件,不是为了排斥临摹,而是为了给后人留一把最原始的标尺。
近几年,小学书法课陆续把毛主席诗词列入范本,孩子们握着硬笔写“红军不怕远征难”,锋芒收敛,气口尚在。业内评价,这种“硬笔毛体”既保留运笔节奏,又符合现代书写习惯,是对传统的一次适应性延展。

诚然,毛体风潮中不乏浮躁之作,动辄标价高昂,甚至套用“国礼”噱头。但真正的好作品,还是要像李坤泽那样,沉下来,摹骨架,悟气韵,再融入个人性情。只有这样,写出来的线条才有呼吸感,不是一味模仿,而是薪火相传。
2
信誉证券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